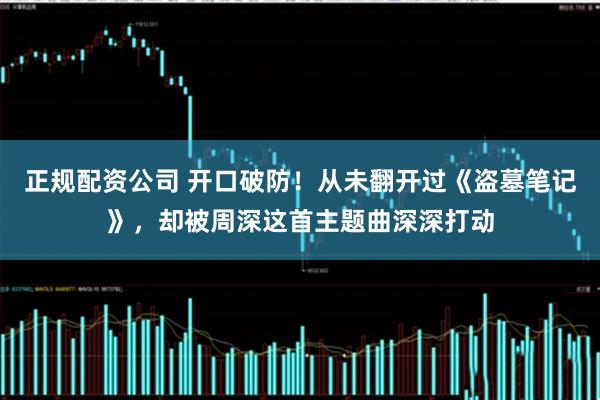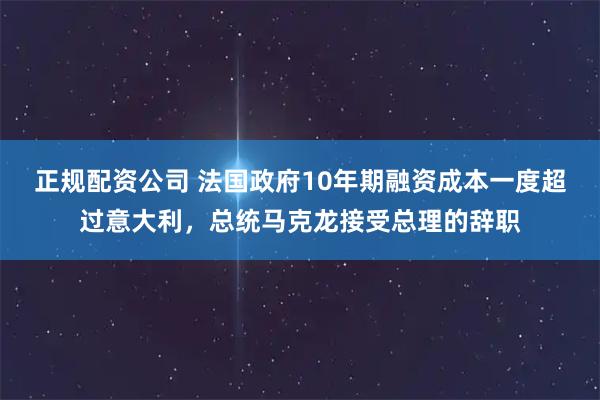暑期档动画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票房口碑双丰收。没有炫酷的3D特效,也没有刻意营造视听奇观正规配资公司,却引发了观众的普遍共鸣,“小妖怪”究竟做对了什么?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专访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监制、艺术总监陈廖宇,听他来聊聊。
无名者的史诗
写给99%的普通人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:4个主角自始至终没有名字。小猪妖、黄鼠狼精、蛤蟆精、猩猩怪……这些以物种命名的角色,构成了一部献给无名者的史诗。
“人类历史上生活过的1200亿人里,能留下名字的可能不足0.001%。”陈廖宇说。在《西游记》的叙事中,小妖们向来是面目模糊的背景板。当这些无名之辈成为主角,他们会偷懒耍滑,会胆小怯懦,会为了“吃口唐僧肉”的小目标奔波,却也在关键时刻守住善良的底线。他们就是无数个普通人,就是无数个“我”。
这种对小人物的凝视充满了人文温度。当小猪妖在决裂时提醒同伴“走没守卫的门”,当蛤蟆精在危急关头为昔日伙伴解围,这些细节勾勒出普通人的精神图谱。
团队在角色设计上也暗藏深意。小猪妖的獠牙故意画得不那么“顺溜”,黄鼠狼精的脸型刻意打破对称,这些不完美的造型恰恰呼应了现实中每个人的独特性。
“生活中我们大部分都是不完美、各有缺陷的普通人。”陈廖宇的玩笑话里藏着他的创作观——有缺陷的普通人更能引发共鸣。
记者:许多观众在影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、日常生活的影子,影片似乎在与当代人的共鸣上下了很多功夫。
陈廖宇:当代性是一把双刃剑。用时髦的流行语、网络词,并不一定有当代性。
这部动画脱胎于传统西游题材,虽以妖怪、山林为故事背景,但一些细节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。
比如小猪妖“让家人吃上一口唐僧肉”的朴素愿望,是许多在城市打拼者的奋斗初心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并非只为自己,也是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。
还比如,小猪妖和蛤蟆精辅导猩猩怪的场景,像极了家长辅导孩子功课的“名场面”。
片中一些台词也是我们自己的对话,“你的尊严呢”是我们团队间调侃的日常。
还有黄鼠狼精从“话痨”到“失语”的转变,猩猩怪从“社恐”到勇敢发声的成长等,我们看任何故事,都是在比照当下的自己。
有的故事发生在当代城市,其中也不乏潮流新事物,但可能就是没有当代性,因为它的价值观还停留在过去。
说点网络流行语是表面的,让当代人在情感上得到共鸣共振,才叫当代性。
记者:最近有几部不同类型的片子,都以小人物的视角和普通人的心路历程取胜。这种视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创作题材中,怎么看待这种现象?
陈廖宇:从小人物切入容易有共鸣,但并不意味着选择小人物就一定能成功。故事能否被接受,取决于能否把小人物的故事讲好。如果人物塑造得不好,即便选择小人物视角也没用。
记者:您曾经说,原本小猪妖的结尾可能更现实、更具悲剧性。但现在片子的结尾还是保留了希望,这是一部商业电影的妥协吗?
陈廖宇:这不能叫妥协。我认为每部作品都有它的任务,观众看电影时,既需要揭示生活的真相,也需要安慰和希望。片子里,我们并没有回避小妖怪被欺负、梦想受挫的现实。
大家说小猪妖像自己,只说对了一半。我们能在小猪妖身上看到自己的烦恼、梦想和困境,但他在关键时刻的勇敢和决绝,很多人在现实中未必会如此选择。
影片中的角色做了很多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,给了观众启迪、勇气或一种体验——体验生活还有其他可能,体验“人生有另一种选择会怎样”。
如果最后真的以悲剧结尾,观众会愤愤不平,可能觉得不公。结尾到了那里,需要给观众一个说法,或者说给4个小妖怪写个“评语”,于是拔出4根毛来,给出想象的空间,也是无声的评语。
记者:很多评论说“上海美影厂回来了”,这是个很特别的评价。《哪吒》《罗小黑战记》《雄狮少年》等系列作品也收获了好评,但观众没有这么说。什么样的片子才符合人们对上海美影厂的印象?
陈廖宇:首先,这部片子的主要出品方之一是上海美影厂。
其次,观众可能在片子里看到了与美影厂经典作品中某些一脉相承的东西,比如山林场景的传统画法、自然景观的诗意表达等,有一种细腻的东方美学。
再次,观众对美影厂的情怀以及对中国动画的期待,需要一个情感安放的落点,而这部电影恰好与这种期待有契合之处。所以我更愿意将“上海美影厂回来了”视为一种鼓励和鞭策。
记者:美影厂文脉的传承,具体指什么样的传承?契合点在哪里?
陈廖宇: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创作源泉,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进行发展和变通。
我们今天的作品结合当下时代,作品里的一些现代生活元素让年轻观众觉得亲切。但内在秉承的基于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精神是一致的。
记者:有人总结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历年来的题材,从比较宏观的叙事、英雄史诗逐步向个人价值实现转变。您觉得在这个时代,还能用动画表现宏观叙事、英雄史诗类型的故事吗?
陈廖宇: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和特点。当时的题材契合当时社会的追求;而现在这个时代,个体得到了更多重视,需要表达的机会和空间,创作者身处时代中,其选择自觉或不自觉受到时代影响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叙事就过时了,关键是如何用当代视角去诠释。每个时代就像土壤,会孕育出不同的作品,时代也会像过滤器一样,筛选出符合当下的东西。
作为创作者,忠于自己的内心、作品本身以及作品中的人物,用心去塑造即可。如果整天总结特点、元素,反而会干扰创作。是创作、观众、时代等各方共同作用,孕育出了一部作品。
笔墨意“镜”
当中国画遇见电影镜头
在美术风格的探索上,陈廖宇用一个新概念描述——“笔墨意镜”。这个生造词,表达了团队对中国动画美学的突围思考。
“我们在镜头里注入中国画的风格。”陈廖宇解释道。
在电影中,远处的山岭用写意笔法勾勒,带着中国画的笔墨韵味;而近处的锅碗瓢盆则采用写实手法,让观众能触摸到生活的质感。
这种“大处写意,小处写实”的平衡,既保留了传统美学的精髓,又满足了电影叙事的需求。
实现这种平衡的过程充满挑战。团队在全国找了五六十位美术师,最终筛到十五六人,他们要在2000多张场景中保持风格统一。
一张师徒四人的山间场景,前后画了十几稿才达到要求——既不能过分写实,也不能像纯国画那样脱离镜头空间。十几个人的画,最后还要风格统一。“工业化标准追求统一,而笔墨讲究个性,我们不断在这两者间找平衡点。”陈廖宇说。
就像当下的年轻人,既带着传统文化的基因,又生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样貌。
记者:这部电影没有炫酷的视听,但一帧帧手绘稿把团队焦虑得不行。为什么二维反而比三维更加难画?
陈廖宇:这涉及讲一个中国故事要用什么样式。
必须承认,近几十年来,尤其新一代动画人的基因里包含了很多外来元素。这很正常,当我们相对落后的时候,先向更先进的地方学习。但是,时代变了、技术变了,观众的审美和要求也变了,甚至大家看电影的心态和方式都变了。
我自己生造了一个词儿,叫“笔墨意镜”,是镜头的“镜”。过去,一个横移镜头过来,你看到的是“哇,好漂亮的山水画、中国画”,然后人物在这个画中表演。不是说这不好,但今天电影的观念、审美、观众的观影习惯和需求实际上是反过来的——用镜头去叙事和表达。所以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反过来的——在镜头里加入画意。
同样画一座山,因为采用中国传统的画法,团队经常一个场景画很多遍。我们的美术师其实已经画得非常细、非常像、非常美了,但依然被我否定。为什么?空间透视、光影都很好,但没有中国画的特点。
举个例子,片头的场景,放大细看的话,是一个运动镜头,它所经过的树、山、石头、远处一层层的树,是带笔墨的。
通常,工业化的画法是把轮廓画出来,然后填上颜色,有光影,但是中国画用线条去画一块石头的时候,不光石头要很美,线条也要很美,笔墨也要很有看头。而所有这些,又需要在镜头下呈现。
记者:中国画强调写意气韵,与镜头要求的准确透视、光影、空间并不一致。
陈廖宇:电影中,人在场景里怎么表演,怎么为观众建立一个可信的空间,确实很重要。这个镜头空间包含了实实在在的世界,你能理解的世界,但细看的时候,又带着传统中国画的笔墨和线条。如何处理两者的矛盾?
我们的原则是“大处写意,小处写实”,这样既保留了传统绘画里的气韵,又满足了电影镜头和叙事的功能。
这些是工业标准没法确定的,是人性化的。在制作初期,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不断尝试、磨合,有一段时间真的很焦虑,甚至试过AI。
事实证明,当有特定具体要求时,就能看出来人是人、程序是程序,尽管AI已经努力接近人,但效果真的不一样。
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被我们“折磨”过的所有美术师、原画师、动画师们,特别感谢他们。
这部片子的要求很“麻烦”。不像一般的动画,可能要求画得越准确越好、越光滑越好、越标准越好。而我们在要求动画准确的基础上还要保持一定程度的“手感”,确实非常难画,工作量非常大。
记者:一般认为,电影要有炫酷的视听效果才能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。对动画来说,三维似乎比二维在视听上有更多优势。但这部二维动画并未受此影响,您觉得是什么原因?
陈廖宇: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,但也不完全正确。我们把观众和电影都看得太简单了。
观众去电影院,视听上的不可替代性只是原因之一。一部好电影带来的情感体验、审美感受,在注意力更集中且有仪式感的场合中,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满足,并非只有炫酷的视听才能吸引人。比如,一个人在家看喜剧和在影院与300个人一起看,周围人的反应会丰富自己的观影感受。
所以,并不只有突出的视听效果才能吸引观众去影院。归根结底,只要电影足够好,就会有观众去看。
从创作角度来说,动画采用二维、三维还是其他手段,既不是关键也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根据创作需求和目标选用了二维,但并不意味着只有二维才能体现传统文化,比如,《中国奇谭》中也有三维动画,关键是找到最适合表达内容的形式。
好好讲故事
动画的初心与勇气
在谈到镜头语言时,陈廖宇提出了一个朴素的标准:“好的电影会让观众忘记手法,只记得人和事。”在炫技成风的动画行业,这个理念显得格外清醒。
他强调在电影中尽量避免无意义的花哨调度。“不是我们不会炫酷,而是不想让技巧干扰叙事。”
当4个小妖在黄眉怪的洞府中面临抉择时,简单的镜头切换反而更能聚焦人物的内心挣扎;当猩猩怪终于喊出“我是齐天大圣”时,克制的镜头语言让这一刻的情感爆发更具力量。
“我们从没刻意分析年轻人喜欢什么,因为创作者本身就是观众。”
真正的共鸣不需要刻意讨好,当创作者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困惑与情感体验时,自然能在作品中传递出与观众相通的精神密码。
记者:不追求炫酷,就是讲好一个故事——靠这一点来吸引人看电影,是需要底气的。
陈廖宇:今天的电影,镜头难免穿插、摇移、推拉、上天入地、大旋转,甭管二维三维动画,都在玩这些东西。我没觉得这不好,观众是需要视听刺激的,但每一部片子、每一个团队、每一个品牌IP,都有它自己的调性。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的调性要从《中国奇谭》说起。《中国奇谭》创作之初,我就跟所有导演说,要好好讲故事,不是不可以炫酷,但不要为了炫酷而炫酷、为了炫技而炫技,首先要讲一个好故事。
当然我也理解,作为一部电影,到高潮戏,到一些桥段,我们也有特美的画面、炫酷的打斗。但炫酷的打斗里仍旧要去塑造人物,去叙事,去呈现这4个草根妖怪的人物形象。即使他们对战终极大boss,他们的手法、打法也跟常见的英雄不一样。所以最终还是尊重故事,把人物本身放在第一位。
记者:目前票房成功的中国动画电影,基本上都采用传统叙事,把故事讲好。但也有一些艺术、先锋、小众的动画电影,采用非传统叙事手法,可能没有高票房。在这个时代,它们还有生存空间吗?
陈廖宇:我认为都有生存空间。“电影就应该讲好一个故事”这句话有前提,即当电影面向市场和广大观众时,讲好故事很重要。
抛开这个前提,电影艺术本身需要多样性,有叙事的、意识流的,常规叙事的、非常规叙事的等等。这些不同形式的电影,数量和比例可能不同,但都有存在的理由,这样,电影艺术才能健康、有生命力地发展。
有些独特的作品就像试验田,能为行业提供新的思路。如果电影只剩一种形态,就会走向僵化和衰亡。
记者:但叫好有时候不一定叫座。
陈廖宇:关键是创作者和出品方要清楚自己的选择,是面向市场,还是进行探索实验,并且对选择的后果有心理准备。做先锋动画就要接受票房可能不高的现实,但可以参加国际电影节、进入艺术院线。
只要在创作中找到与自身、他人和社会的契合点,所有形式的电影都有存在的机会。
记者:比如《中国奇谭》中“鹅鹅鹅”这个晦涩、深奥但又好评度很高的小故事,有可能改编成动画电影吗?
陈廖宇:没尝试过的事情,不要轻易断定可行与否。任何风格的探索都是值得的。
“鹅鹅鹅”当时只有创意时,大家对它的看法也充满争议和担忧,觉得它太个人化、小众、晦涩。但事实证明,大众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度很高。
所以,我们需要做一些不确定的探索,甚至接受失败或不完美的结果,就像小猪妖一样,即便结果未必成功,但尝试和努力本身就有意义。
记者:国产动画现在的工业化体系、流程,是不是已经追上了全球水平?
陈廖宇:我只是行业里的一个具体创作者,接触到的面有限,不能代表国产动画整体。只能说,这些年我们在观念、技术、作品完成度、导演意识等方面都在快速进步,处于上升期。
实际上,全世界动画做得好的国家不多,一只手就数得过来,中国肯定在其中。不同国家各有优势和风格特征。
中国动画正处于蓬勃发展期,在各个领域、风格、门类上都有发展,尚未形成特定印象。这也是好事,意味着中国动画还有无数可能。
就像美影厂老前辈常光希老师说的,“中国动画的探索一直在路上”,我们也在取经的路上。
陈廖宇
北京电影学院教授,动画导演,《中国奇谭》总导演。中国传媒大学、浙江传媒学院、郑州轻工业学院客座教授,北京市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,东布洲国际动画周策展人。
原标题:《专访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主创:写给99%的普通人》
来源:作者:解放日报 龚丹韵
高亿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